应对基孔肯雅热 蒲松龄《驱蚊歌》道出中药妙用

近日,基孔肯雅热在多地传播,备受关注。基孔肯雅热是由基孔肯雅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,通过伊蚊(俗称花斑蚊)叮咬传播,症状以发热、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。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困扰。
中药驱蚊古已有之。几百年前,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一首诙谐的《驱蚊歌》,道尽了蚊虫的危害与古人的驱蚊智慧。通过这首诗,我们不仅能领略古人的生活趣味,更能认识到中药驱蚊的价值。全诗如下:
夏蚊长喙毒于蝇,薄暮暗室如雷轰。
摇身鼓翼呼其朋,翩然来集声嘤嘤。
衾覆半体啮股肱,皮肉坟起爬枨枨。
雏者将至飞且鸣,猾者潜来无形声。
私心窃幸遂贪情,床头才觉腹已盈。
露筋女郎全节贞,小物虽小累大清。
炉中苍术杂烟荆,拉杂烧之烟飞腾。
万翼塞户相喧争,屋烟既尽仍骄狞。
檐穴之砂号夜明,碎而细视皆蚊睛。
安得蝙蝠满天生,一除毒族安群氓!
诗中说蚊子凭借它的“长喙(嘴)”比苍蝇还狠毒,每至薄暮时分,它们群集暗室,摇身鼓翼,呼朋引类,鸣响如雷。它们寻隙叮人,令人防不胜防,人们用被子盖住半边身体,它们又去咬另一半的腿和胳膊,咬得人身上“皮肉坟起”,让人不住地爬搔,发出“枨枨”的声音。幼小的蚊子“飞且鸣”,而那些狡猾的成蚊却悄悄地飞到人身上,它们暗自窃喜,尽兴吸吮,遂了它们的“贪情”,等到床上的人发觉,它们早已经饱吮人血,肚子胀得很大了。别看蚊子很小,对人们的危害却非常大。诗中引用了“露筋女”的典故,据传说,唐代高邮一女郎避乱,日暮行于荒郊,女郎为保贞节,露坐草丛中,不堪秋蚊叮咬,血竭筋露而死。后人哀而为之立祠,号“露筋女”。
面对蚊子肆虐,诗人又写了驱蚊的方法,即用苍术等植物混合在一起,焚烧生烟来熏蚊子。千万只蚊子被熏得挤在一起“相喧争”。屋里烟尽之后,那些未被熏死的蚊子又重新活跃飞腾起来,仍然骄横凶恶。人们从夜明砂(蝙蝠粪)里发现有些未被消化的蚊子的眼睛,得知蝙蝠有食蚊之功,于是寄希望于蝙蝠,希望蝙蝠满天而生,将蚊子吃光,使黎民安生。
诗中提到的“炉中苍术杂烟荆,拉杂烧之烟飞腾”,是古代驱蚊的常用方法。将苍术、艾草、菖蒲等植物混合或编织成绳,点燃后以烟雾驱蚊。明代方孝孺在《蚊对》中也有类似描述:“童子拔蒿束之,置火于端,其烟勃郁,左麾右旋,绕床数匝,逐蚊出门。”这种烟熏驱蚊的方法,其原理是基于中药的芳香辟秽与物理驱避作用。
中医古籍中也有很多类似的驱蚊方,如《普济方·卷二百六十八·杂录门》中的“祛蚊法”:“香附子、苍术半斤,雄黄(别研)、樟脑(别研)各半两,右为细末,入雄黄、樟脑和匀,重罗,打作香印,爇之。”
《本草纲目》引孙思邈验方:五月取浮萍阴干。《卫生易简方》:浮萍、羌活为末,焚之,蚊自绝。《外治寿世方》:取池中浮萍晒干,晚间与苍术、白芷同焚,蚊感其气,悉化为水。
方中的苍术味辛、苦,性温,能燥湿健脾,祛风散寒,具有芳香辟秽的功能。现代研究表明,苍术含多种挥发油,主要成分为β-桉叶醇、苍术酮和苍术素,这些成分可能通过熏蒸作用干扰蚊虫的嗅觉或神经系统,起到驱蚊的作用。艾草驱蚊作用也很强,陆游《熏蚊效宛陵先生体》诗云:“泽国故多蚊,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,燔艾取一快。”现代研究表明,艾草含桉叶醇、β-芹菜醇、植物醇等成分,对按蚊具有显著熏蒸毒性和驱避活性。其中桉叶醇熏蒸毒性最强,10分钟内可致蚊死亡。
诗中所说的荆是指黄荆、牡荆一类的植物,其味微苦、辛,性温。《本草纲目》引《物类相感志》云:荆叶逼蚊。至今南方农村仍保留焚烧荆条驱蚊的传统。
浮萍、石菖蒲等药物能芳香辟秽,解表化湿,也是驱蚊常用药物,其药理作用仍待进一步研究。需要注意的是雄黄加热释放的三氧化二砷虽有驱蚊效果,但存在毒性风险。
现代通过中药提取与缓释技术结合,可以将上述药物制成驱蚊贴、手环、喷雾、凝胶等,使传统方法更适合现代生活。
也可将这些中药制成香囊佩戴,选艾叶、苍术、菖蒲等少许,打成粗末,装入布袋中做成香囊,带在身上或悬挂床头,避免了化学驱蚊剂可能带来的刺激,尤其适合儿童、孕妇等人群。
诗中所说的“蝙蝠满天生”则蕴含了生物防治的理念。蝙蝠以蚊为食,一只蝙蝠每夜可捕食三千只蚊子,堪称自然界的灭蚊卫士。古人也有用夜明砂焚烧熏蚊子的,如《卫生易简方》云:“夜明砂与海金砂,二味同和苦楝花,每到黄昏烧一捻,蚊虫飞去别人家。”
蒲松龄的《驱蚊歌》不仅是一首文学作品,更是一份古代卫生习俗的珍贵记录。中药驱蚊作为一种绿色、环保的方式,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,彰显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。(谭洪福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东关社区卫生服务站)
推荐资讯
- 玉雪肌肤纯阳果2025-08-03
- 江苏中医的历史发展与群体特点2025-08-03
- “药王”孙思邈与龙山的渊源2025-08-03
- 应对基孔肯雅热 蒲松龄《驱蚊歌》道2025-08-03
- 夏日鳝鲜胜参茸2025-08-03
- 全国卫生健康技术传承项目:中医气2025-07-31
- 文史丨亲自诊病开药!宋仁宗这样推2025-07-28
- 醋韵龟龄:山西醋膏与龟龄集的药香2025-07-24
- 香囊:千年风雅里的东方美学与生活2025-07-03
- 承中医外科之魂 弘大医精诚之道 ——2025-07-03
快捷留言
名医名家推荐

- 健康牛穴位戒烟诚邀加盟
- 投资额:1-5万
- 热度:

- 我要加盟
- 健康资讯
- 针灸艾灸
- 苗医苗药
- 全国卫生健康技术传承项目:中医气血疗法项目
- 醋韵龟龄:山西醋膏与龟龄集的药香传奇
- 热茶消暑意自凉
- 便秘分虚实 辨证施养更有效
- 湿未重,暑未酷 小满食养正当时
- 警惕“记忆橡皮擦” 饮食防治阿尔兹海默病
- 嗓子疼痛了?速食疗养生法,让你快速恢复!
- 男宝宝体虚调理指南:让宝宝健康成长的新选择
- 夏日养生:远离湿气的食疗之道
- 健脾胃除湿的食材推荐与食疗指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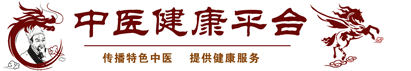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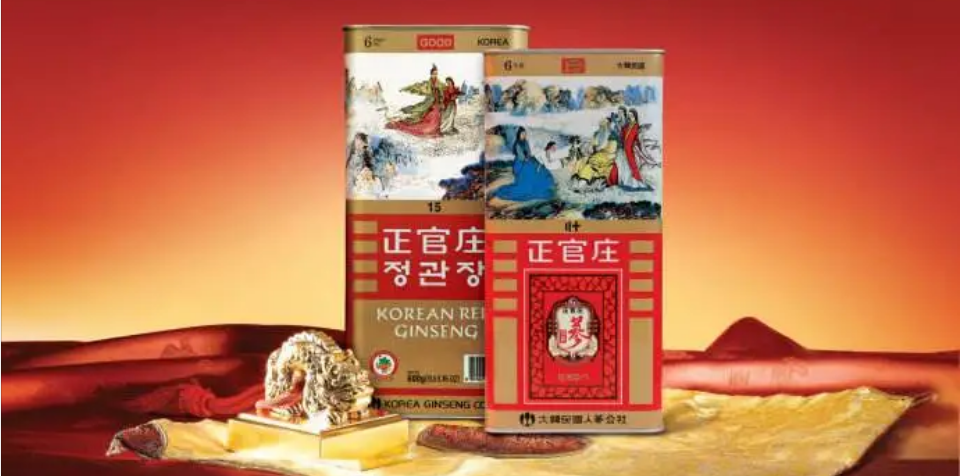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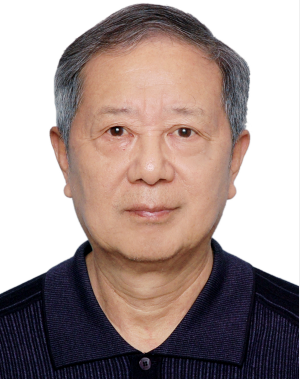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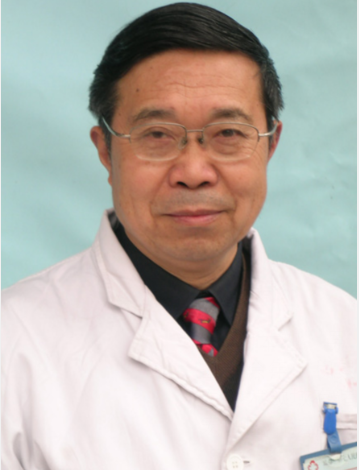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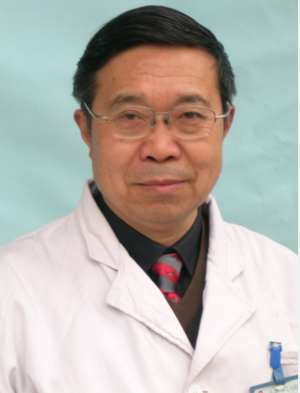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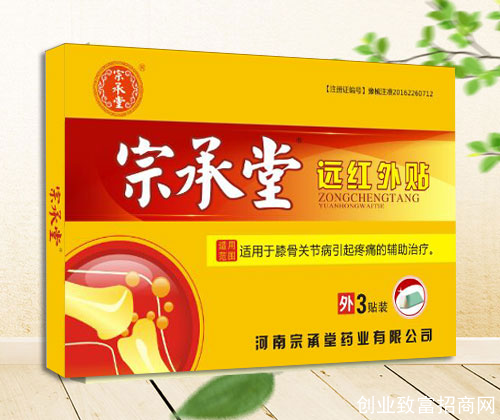





我要加盟(留言后专人第一时间快速对接)
已有 18379 宣传人民健康生活和健康产业的权威媒体新平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