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秋食薯话闲情

“初秋至,秋风软”,浙江富阳的初秋总裹着层江潮的水汽,晨露还沾在薯叶上时,巷口铁皮桶便冒出第一缕白汽——那是烤红薯的甜香,像根温软的引线,牵出了江南秋日的烟火味。这味道藏在乡间田垄里,沾着泥土的红薯刚被挖出,转身就能变成餐桌上的暖食,熨帖着刚褪去暑气的脾胃。
这时节的乡间田埂最是热闹。红薯藤匍匐在沙土地上,深绿的叶子间缀着零星淡紫小野花,风一吹就晃出细碎的影子。农民握着锄头,在藤根旁轻轻一刨,湿润的沙土被翻开,圆滚滚的红薯便露了脸——有的浅红如蜜蜡,有的深紫似玛瑙,沾着泥的薯皮上还挂着细细的根须。小孩跟在后面,伸手扯住藤蔓一拉,偶尔拽出个拇指大的薯仔,擦去泥土就想咬。大人笑着说:“要蒸透了才甜,急什么!”田埂边堆着的红薯晒在阳光下,泥土慢慢变干,淡淡的薯香混着风里的青草气。
关于红薯,明代徐光启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记载:“甘薯所在,居人便有半年之粮,民间渐次广种”,清晰勾勒出这一原产美洲的作物经菲律宾传入江南后,成为百姓饱腹之物的场景。《本草纲目》更精准描述其特性:“味甘、性平,补虚乏,益气力,健脾胃。”富阳中医养生馆里坐堂的老中医常叮嘱街坊:“初秋燥气盛,别总喝凉茶,蒸块红薯最养脾胃。”夏天贪凉吃多了生冷的人,喝碗掺了干百合的红薯粥,润肺又暖肚,这是老祖宗传下的食疗方。在富阳乡间,常有老人捧着粗瓷碗,就着自家腌的咸菜喝红薯粥,嘴里念叨着“秋吃薯,冬不苦”。
初秋的富阳街头,最勾人的莫过于烤红薯的香。铁皮桶被炭火烤得发黑,老板掀开盖子时,白汽裹着甜香涌出来,能飘半条街。选红薯要挑圆胖的,表皮光滑没裂痕,老板用铁钩拉出来,在桶边轻磕掉残留的浮土,裹上张牛皮纸袋递过来。掰开的瞬间,蜜色的薯肉泛着光,靠近皮的地方还带着点焦脆,咬一口,甜汁顺着嘴角流,烫得直呼气,却舍不得停嘴。如今路过巷口,我总爱买一块捧在手里,指尖裹着暖意,偶尔想起儿时和母亲分食的模样——那时手指沾着薯泥,舔一舔都是暖的,江风拂过,连甜香里都掺了几分清爽。
富阳人在家食薯,最常做的是红薯粥。砂锅里的本地晚米淘洗干净,加足量水大火烧开,转小火慢炖得米粒开花。红薯去皮切成块,等粥炖得黏糊了丢进去。熬到红薯化在粥里,粥色染成金黄,盛一碗放凉些,入口糯滑,甜而不腻。清晨喝一碗,胃里暖暖的;傍晚配着酱瓜吃,解腻又舒服。寻常人家煮红薯粥时,总爱多煮些,端一碗给左邻右舍,热气腾腾的粥里,藏着乡邻间的温情。
宋代苏轼曾有诗咏“半园荒草没佳蔬,煮得占禾半是薯”,恰是这寻常人家以薯为食的生动写照。有的人家会把红薯切成条,晒在自家屋檐下,阳光晒得薯干发亮,甜香飘满院落,留着冬天当零食,嚼着还能想起秋日暖阳。
待秋风渐渐有了凉意,手里握着烫手的烤红薯,或是喝着一碗温热的红薯粥,心里都是暖的。这红薯藏着初秋的温厚,从乡间田垄的泥土香,到寻常人家的餐桌烟火气,每一口都是江南初秋的味道。不必讲究什么排场,只在微凉的风里,品一口甜糯的红薯,便觉这初秋的日子,格外惬意绵长。(李治钢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科学技术协会)
推荐资讯
- 祛湿良方“红豆薏米汤”你真的吃对2025-09-29
- “脆皮年轻人”有救了?“散装养生2025-09-29
- 中医药缓解便秘办法多(中医养生)2025-09-29
- 过敏性鼻炎重在治本(中医养生)2025-09-29
- 这些人 吃水果悠着点2025-09-29
- 益生菌的正确用法很多人没做对2025-09-29
- 长假过后容易身心不适 疾控提醒:避2025-09-29
- 如何在运动和健康生活中自然减重2025-09-29
- 惊蛰时节饮食宜“减酸增甘”2025-09-29
- 好气色靠“养”不靠“妆”2025-09-29
快捷留言
名医名家推荐

- 健康牛穴位戒烟诚邀加盟
- 投资额:1-5万
- 热度:

- 我要加盟
- 健康资讯
- 针灸艾灸
- 苗医苗药
- 祛湿良方“红豆薏米汤”你真的吃对了吗?
- “脆皮年轻人”有救了?“散装养生”正在流行
- 中医药缓解便秘办法多(中医养生)
- 过敏性鼻炎重在治本(中医养生)
- 这些人 吃水果悠着点
- 益生菌的正确用法很多人没做对
- 长假过后容易身心不适 疾控提醒:避免熬夜 减量
- 如何在运动和健康生活中自然减重
- 惊蛰时节饮食宜“减酸增甘”
- 好气色靠“养”不靠“妆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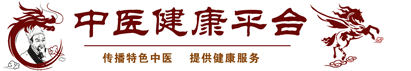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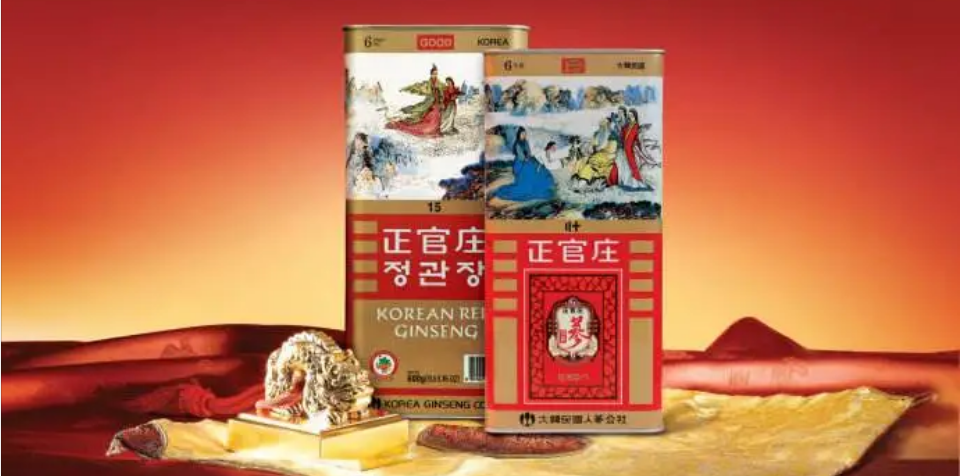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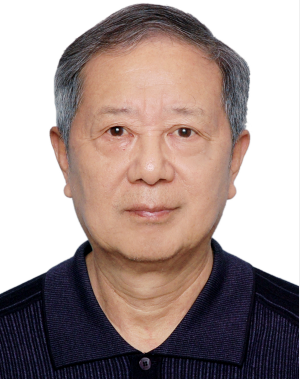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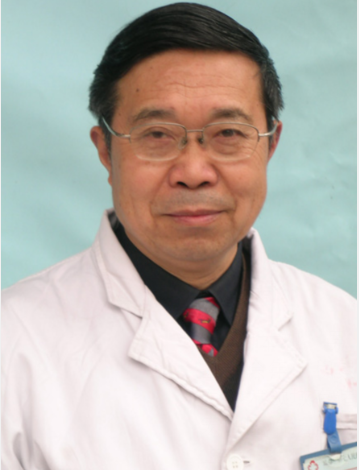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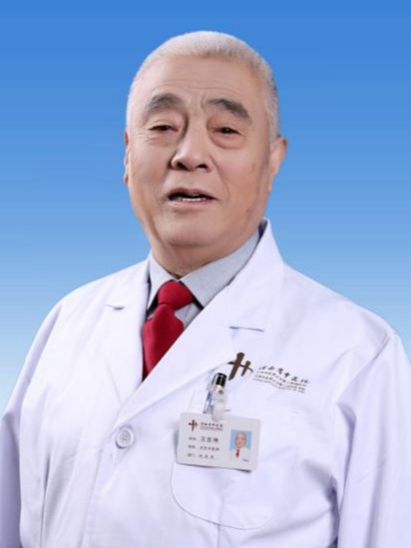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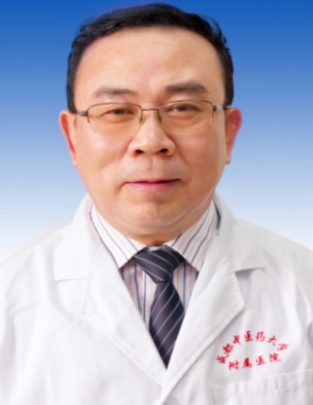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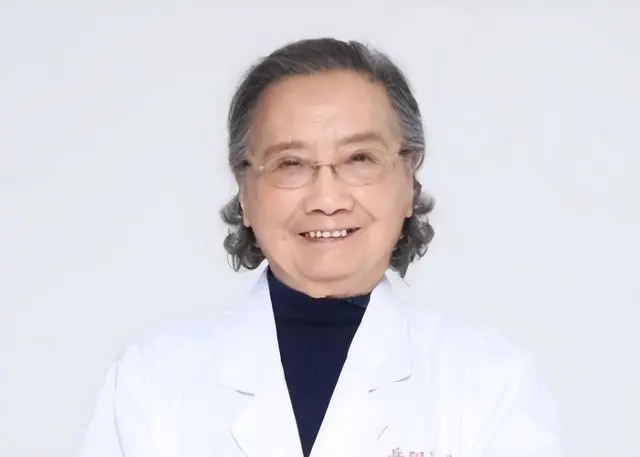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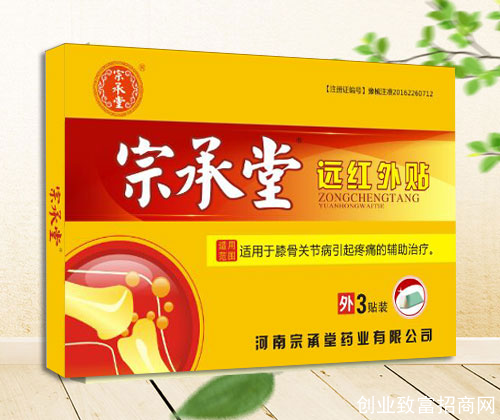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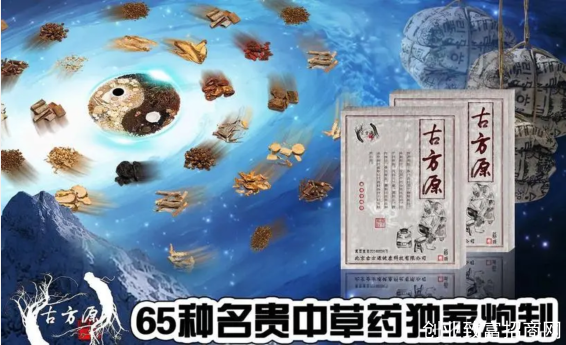


我要加盟(留言后专人第一时间快速对接)
已有 18379 宣传人民健康生活和健康产业的权威媒体新平台